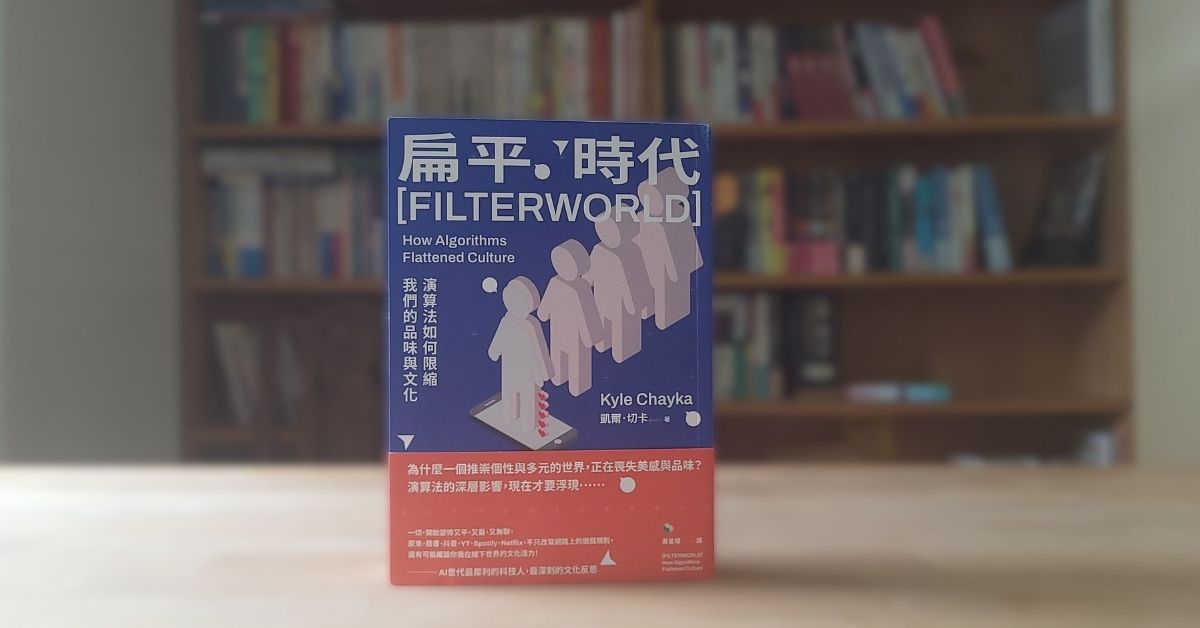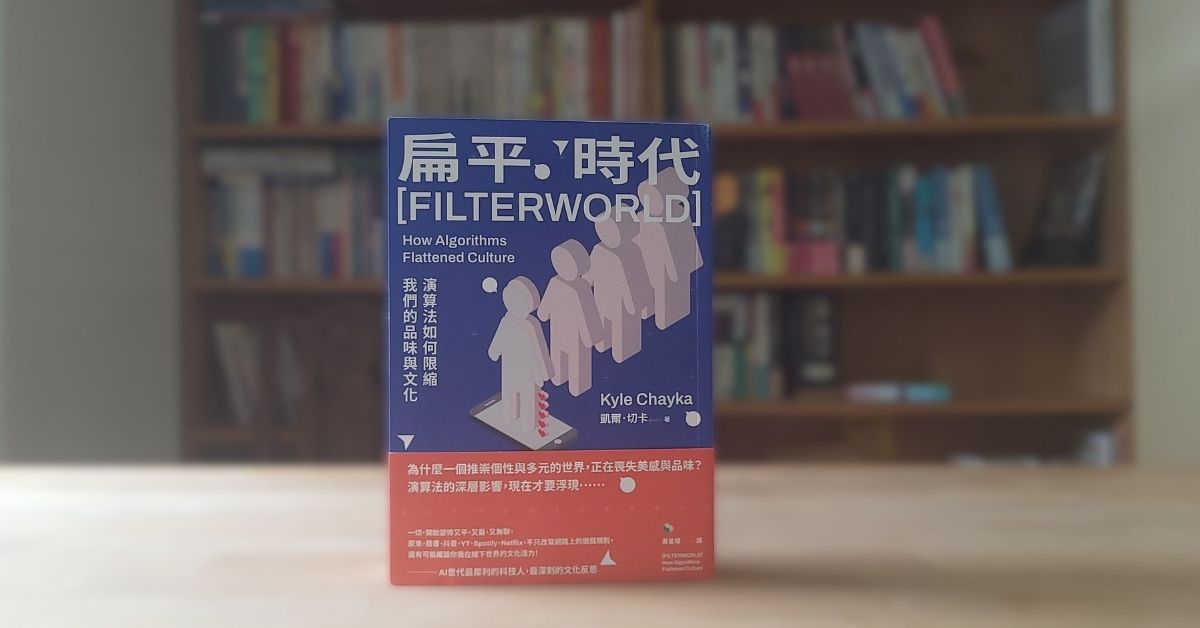隨著社群媒體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流、認識重要的工具時,許多人在各種資訊查詢、研究也越來越依賴這些工具,不過,當時代越來越進步的情況下,每個人能以更多元、自由自在的方式形塑個人特色與風格,然而這世界的審美、思考模式卻逐漸單一又無趣?
這些原因可能出自於我們開始只閱覽演算法推薦給自己的貼文內容,被演算法所掌握,也只能夠看見演算法「期望」我們看見的事物,這導致人們逐漸喪失鑽研某項事物、細細品味的餘韻,喜好也越來越相似。
衛城今年一月出版了《扁平時代》,這本書認為社群媒體與串流平臺的演算法,讓文化變得愈來愈扁平一致。為了回應這個許多人都深有共鳴(往往也深感苦惱)的問題,衛城特別邀請《新活水Fountain》總編輯黃麗群,以及獨角獸計劃創辦人李惠貞,針對本書的觀點,從各自豐富的文化工作經驗出發展開對談。
▌人類對科技最大的反思
過往,我們可能會為了一件事情細細鑽研、品味,然而隨著社群媒體、AI世代的崛起,演算法掌控我們閱覽資訊的來源。
這使大眾的偏好越來越一致,造就「扁平時代」,本書對於該現象進行深刻反思,分析從未多想的數位現實。
▊作者
凱爾.切卡(Kyle Chayka)
《紐約客》專欄作家,書寫主題包括數位科技以及社群媒體對文化的影響。二○二○年,他出版了首部非虛構著作《渴望極簡》(The Longing for Less)。在這本書裡,切卡探索了生活和藝術領域當中的極簡主義風潮。
切卡也是一名新聞工作者和評論人,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哈潑雜誌》與《新共和》等媒體。此外,他也是線上藝術雜誌《Hyperallergic》的首位專職作者。
「投其所好」vs.「出其不意」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講座一開始,黃麗群就拋出一個挑戰這本書的問題:就像《扁平時代》所說的,這些科技公司不會透露演算法背後的邏輯,那麼我們如何推斷出它會導致扁平的結果?她認為扁平的現象確實存在,演算法也有其作用,但推動整體趨勢的力量與成因還有待釐清。「究竟是演算法讓我們變得扁平,還是追求最大化注意力這件事,讓我們的心智被凹折成會去追求那個方向?」作者切卡也不諱言自己會關注貼文的按讚與分享,科技媒介與人性傾向的交互影響,成為本書開啟的思考點之一。
李惠貞則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演算法與人們集體心理的關係。她提到,雖然在今日的網路時代,我們面對的是演算法,但這本書描述的情況不是現在才發生。這些社群與串流平臺的行銷手段展現出來的,其實就是廣告的本質。「廣告就是投其所好,勾起消費者的興趣讓人買單,這些網路巨頭也是在做一樣的事。只是透過演算法,它們可以更快找到受眾。」扁平時代的危機在於,這些誘人的選項來得又多又快,吸引人的力道也增強了,消費者變得非常被動,扁平來自主動選擇、過濾的空間與時間被壓縮。
「演算法雖然是投其所好,而且看似為你量身訂做,但它對每一個人的瞭解其實是非常表淺的。」李惠貞說。人們如果只是接收大眾的喜好,往往無法深入探索自身複雜的面向,而這本書最後提出策展概念作為對照,便是一種避免讓品味流於表層的方式。她認為,好的策展就是「出其不意」,挑戰觀看者原先的眼界,策展的「出其不意」與演算法的「投其所好」形成鮮明的對比。《扁平時代》對這些現象的觀察與反思因此是很好的提醒,讓我們在享受網路時代帶來的好處的同時,也能對背後的商業機制多一分警覺,進而找出應對的方法。
▌更多脫離社群媒體掌控的方法
主動參與、主動「調教」演算法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那麼,我們要如何在這個一不小心就走向一致的時代,維持彼此之間的多樣性呢?李惠貞的答案是:閱讀。對她來說,閱讀是一個主動參與的過程,每個人對同一本書的感受和想法都不一樣,自己個性的特質會隨著閱讀浮現,展露出人的多樣性。
如果真的必須跟演算法打交道,也有許多制衡的手段。黃麗群感嘆「人類科技的近用性,和社群媒體所創造出來的環境,導致我們現在一天要處理的資訊量史無前例的多」,為了降低自己的認知負擔,她除了手機不開通知之外,更會訓練演算法,讓它只推薦特定的內容。對黃麗群而言,最大的困擾不是同質性,而是劣質的東西太多。在這些泥沙中可能存在少數珍貴的事物,但就需要花費心力在實體或數位世界中掏金,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有好奇的欲望或探索的精力。
或許問題出在現代社會的轉速,已經讓人無法好好的、慢慢的消化某些精細的內容。黃麗群以這本書提及的、人們再也沒辦法從頭到尾聽完一張專輯的現象為例,說明這件事依然可行,只是現代人已經鮮少擁有這樣的餘裕。
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對了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在好壞內容紛雜並陳、資訊過載的現實環境下,要找回創造與享受文化的餘裕,似乎愈來愈困難,卻也不必絕望。李惠貞說,重要的是在利用演算法這項工具時,不能為了流量而離自己當初的目標愈來愈遠。獨角獸計劃的粉專經營方式就相當老派,也沒有特意迎合演算法,反而讓自身的獨特面貌被看見。
企劃思考也是如此。從想回應的問題出發、邏輯清晰的企劃,足以抵禦社群時代可能的亂流與雜念。李惠貞同樣舉獨角獸計劃的例子,她的初衷是推廣閱讀,在這個前提之下,她發現臺灣不缺好書、不缺好的書店,缺的是讀者,於是目標就變成「要讓讀者回來」,要解答的問題則是「讀者為什麼會流失」。一個很經常的回應是因為忙碌沒空閱讀,她便告訴讀者忙不是問題,閱讀不一定要看完一本書,沒看完就看下一本也沒關係。關於企劃,她總結道,首先是人們永遠要知道為什麼要做某件事,再來才是方法與技巧,而包括網路在內的任何科技都可以是我們的方法,端看我們怎麼運用。想得夠清楚,溝通才會有力道,若再搭配上好的方法,無論多麼小眾的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受眾。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黃麗群對於「如何發想出好企劃」的回答則充滿看破現實的豁達。她表示,不管是推廣閱讀,還是編輯雜誌,都會遇到一個難以對抗的困境:「這些科技公司是花大把的時間精力、聘請菁英在駭大家的腦,針對我們還沒有跟著科技同步進步的腦神經迴路跟人性,踩著人的弱點去拿捏。」所以在黃麗群看來,我們也不能多想什麼,只能做自己想做、喜歡做的事情。
她分享自己多年前曾經做過另一本雜誌的臺南專題,當時跟同事還有攝影師規劃好要拍的地方及動線後,就到臺南玩了一天,玩得很開心、拍攝的成果也非常漂亮,於是她決定讓照片說話(沒寫太多文字的她出刊時還有點心虛),結果這期成為所有她做過的主題裡,同事和焦點團體最喜歡的一個。如同《扁平時代》提到好的作品未必流行、流行的作品也未必不好,努力做的作品不一定會受歡迎,反之亦然。受眾反應未知的情況下要不虧本,就只能做自己真心好奇、有興趣的題目,這樣即使不受市場青睞,仍然完成了一件當初想做的事;而且就像臺南專題的經驗顯示的,這種真心喜歡某件事情的能量,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感染力。
更有意識的活,就永遠有新的可能性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講座最後,兩人討論到策展在當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李惠貞覺得好的策展是熟悉脈絡的策展人,針對某樣事物提出自己的問題或觀點,引導出觀者複雜而豐富的面向,書店與雜誌其實也是廣義的策展,透過書籍與內容的擺放,呈現出企劃人的視野;相比之下,演算法就像填鴨式教育,只是不斷塞給人們答案,背後卻缺乏問題與脈絡。
黃麗群也認同好的企劃或內容,帶給受眾的應該是問題而非答案,不過與其說策展人,她更將自己定位成「說故事的人」。她認為編雜誌就是說故事的過程,藉由閱讀動線的鋪展、結構的安排與節奏的設計,把一個故事說好。至於策展的定義,她笑說自己決定家裡的花要怎麼擺也是一種策展,每個人都有生活的一套邏輯,這跟策展的本質是相通的,只是過去策展時常會跟文化菁英聯想在一起。
順著策展的話題,李惠貞表示《扁平時代》裡對策展的描繪帶給她許多靈感,對品味的闡述很容易理解又切中核心,是她書中最喜歡的兩個段落。同時她也提醒大家,現在固然每個人都可以是策展人,但社群媒體的讚數、留言與分享等獎賞制度,時常使人落入追逐流量的陷阱而無所適從。最終是受益還是受制於科技,取決於自己的選擇,不能只怪罪給演算法。對她而言,如果參與網路的交流會影響到她對生命的追求,就必須做出調整或取捨,「我們必須更有意識的活,更有意識的參與我們所選擇的事情,如果這件事會傷害到我本來的初衷,那肯定是我用的方法不對,必須尋找新的方法或可能性。我相信永遠有新的可能性。」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提供
在提問環節,兩人也分享了她們通常怎麼得知好書的存在。由於網路上充斥的總是時下討論度最高的書籍,黃麗群只能依靠經常分享書訊的朋友推薦等口耳相傳的方式獲取新知。李惠貞則鼓勵大家時不時就要去書店走一走,那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其實關注或感興趣的主題,會在逛書店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的被召喚出來。
雖然演算法確實對文化產業造成不少影響與衝擊,但兩人的過往經驗與思考路徑,為所有深陷演算法迷障的人們帶來希望:要運用網路作為工具,就必須瞭解它的規則,卻不是非迎合演算法不可。在創作與接收內容時掌握本心,提高自己的主動性,立體與多樣的可能一直都在。
✦
▌學習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