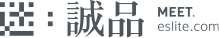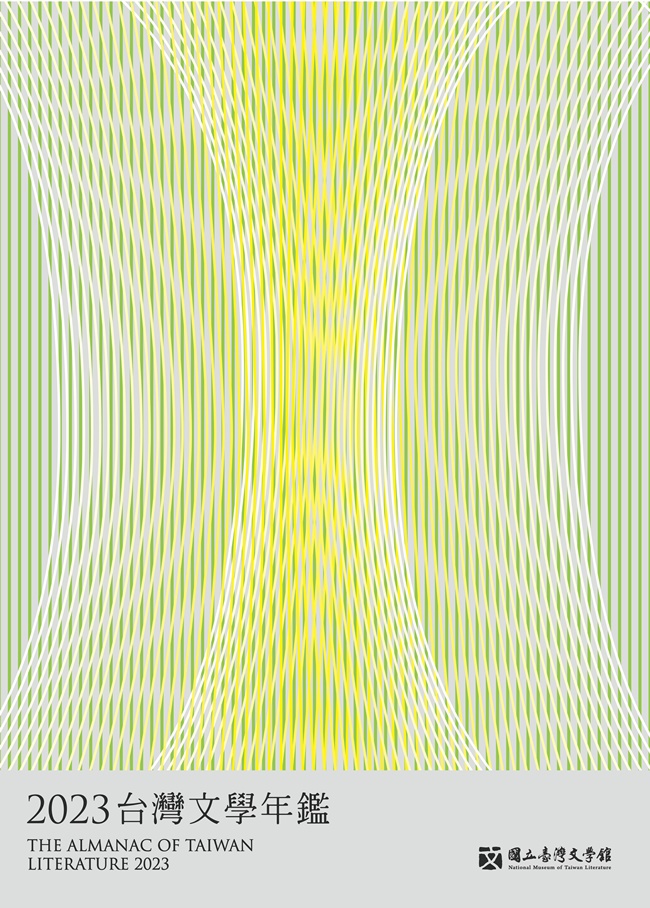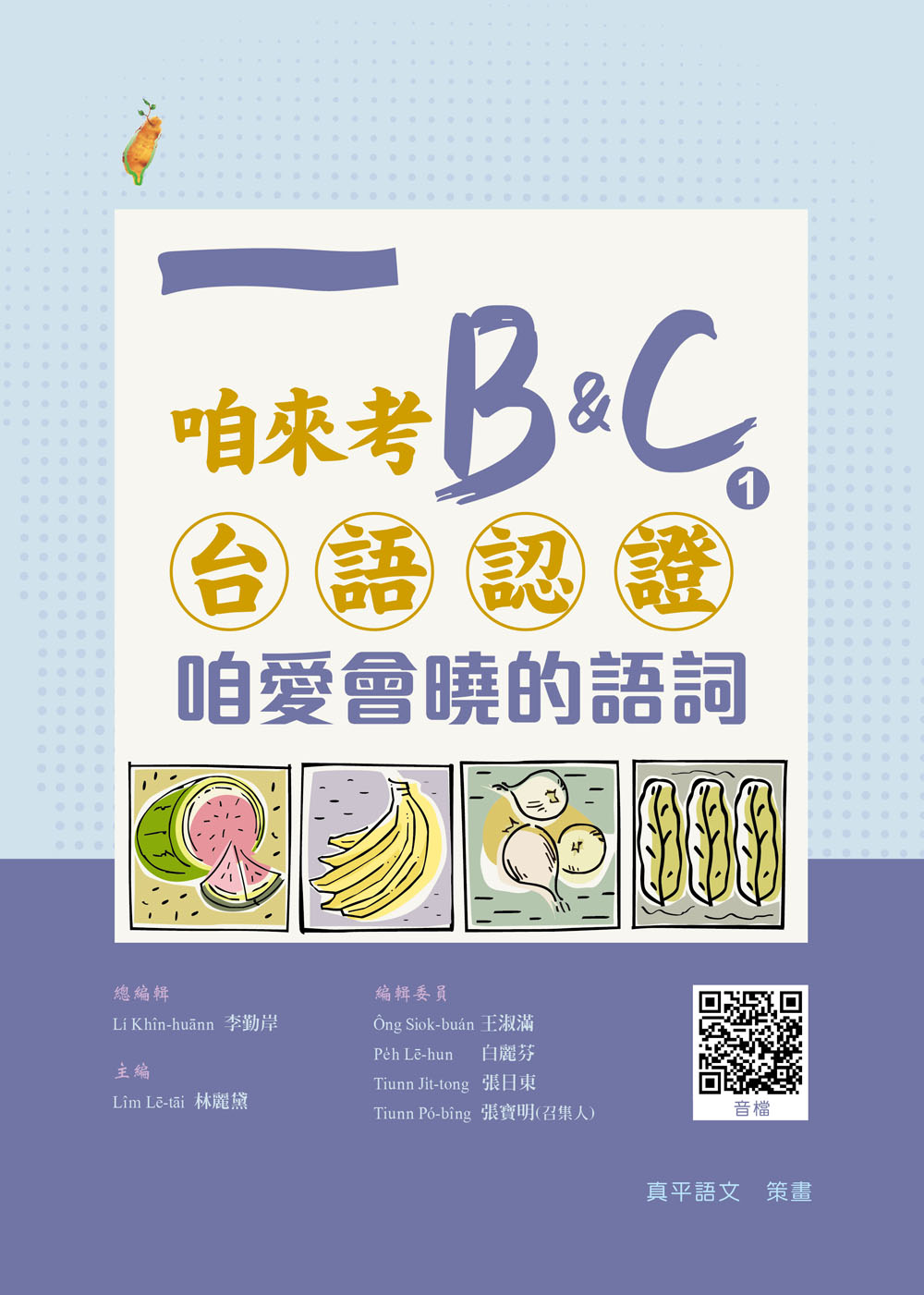謝銘祐:台灣文學在我的成長過程裡面,是從隱形到慢慢浮現|台灣文學慢板
撰文 劉怡青❝我也開始發現葉石濤的寫作的風格,好像是有一大塊鐵片壓在他的頭上。我一直覺得他是隱身想告訴看書的人,其實我很沉重。因為每一篇作品交出去之前,都是要被檢查過的。❞
延續誠品生活台南開幕展「寫予時間的記持:台灣文學慢板 siá hōo sî-kan ê kì-tî」,我們邀請四位與這座城市有深刻緣分的台南人——謝銘祐、謝仕淵、林秀珍、台南妹仔ayo——說一段他們被台灣文學找到的故事。
文學,或許曾被掩蓋、遺忘,卻在某一刻悄悄地來到身邊:是少年時讀懂葉石濤筆下的壓抑,是童年睡前爸爸讀唸的床邊故事,又或是課間選讀篇章裡,看見社會邊緣生命的真實處境。書頁裡的文字始終安靜,卻一直流動於人與城市之間,像一條水路,靜靜地,帶來記憶與修復。
在這裡,讓我們與台南人一起,回到他們閱讀台灣文學的源起之處。
「行 沿路行 行 慢慢行⋯⋯」如果你曾在台南的圖書館待到閉館,那一定聽過謝銘祐〈行〉這首溫柔的歌。〈行〉收錄於2012年發行的《台南》這張專輯,自稱「府城流浪漢」的歌手謝銘祐,五歲搬到安平後便在台南一路成長,直至離鄉念大學、出社會擔任音樂製作人在台北生活一陣子,2000年又返回故鄉「繼續行」。
謝銘祐的歌,有著別於其他創作者的故事性和畫面感,他連結小時候第一個閱讀經驗,是媽媽特別買給六歲的他的富蘭克林、華盛頓和居里夫人傳,「那樣的作品我消化得很快。從小就有注意到,我很喜歡去看比較有劇情、很會描述的作品,這樣的閱讀造就了我也是這樣在創作。」同樣也將舞台劇本創作視為志業的謝銘祐,寫歌也像在寫劇本,慣於將情景與人時地的結構融入詞句,彷彿有真實人物行於曲中。
小房間裡的秘密刊物《人間》
談到台灣文學啟蒙,謝銘祐將時間序拉回16、17歲,「台灣文學在我的成長過程裡面,是從隱形到慢慢浮現。」青春期歷經戒嚴後期,日常所讀皆受到限制,在他回憶裡最先露出頭角的是新浪潮電影和羅大佑的音樂,「《兒子的大玩偶》啦,《看海的日子》啦,還有《莎喲娜啦.再見》。我們會因為看到這些電影,回頭去找小說來看。」一系列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著作,在被影像化後傳播力道更廣,影響了一代人的台灣文學閱讀經驗。
當時期這類型的台灣文學,被賦予了「鄉土文學」這個名字。謝銘祐談及當年農村社會朝向工業社會的逐漸轉型,「如果住中南部的人,對台灣還有農業社會的一點印象,但北部工業社會已經浮現一陣子了。」再後來,《人間》這份由作家陳映真創刊,內富含文學性和強烈攝影風格、關注社會弱勢與邊緣議題的刊物,撞進了謝銘祐的高中生活。
❝和老闆熟了之後,謝銘祐開始能接觸到《美麗島》等更多書刊雜誌,「我看《無花果》看到整個驚慌,怎麼台灣有這麼一塊我不知道的歷史?❞
「我念南一中,以前在南一中附近就成大嘛。大學路旁邊有一家書店叫孟子書局,現在不見了。高中的時候,學長會帶學弟,說他裡面有賣一些不一樣哦。」這些「不一樣的」,得熟人去和書店老闆詢問,老闆便會帶人走去旁邊那扇有電流控制的小門。謝銘祐繼續描繪道:「進去了之後,我開始看到一些從沒看過的作者。錢鍾書啦,然後魯迅、羅家倫,有一些書我連聽都沒聽過。我在那個地方買的第一本書叫《圍城》。」
和老闆熟了之後,謝銘祐開始能接觸到《美麗島》等更多書刊雜誌,「我看《無花果》看到整個驚慌,怎麼台灣有這麼一塊我不知道的歷史?哇,然後大量的求知慾就湧進腦袋。我一定要在短時間把這些搞清楚,不然會瘋掉。」於是一本接著一本,或說多本同時輪著看,許多認知在謝銘祐眼前開始瓦解,《人間》也就是在此刻成為影響他最深的一套作品,「他所採訪、拍攝的對象,都是我們日常生活遇得到的阿伯、阿婆,或我們在安平漁村旁邊的移工也好,震撼更大於後來我再慢慢去看的台灣文學,我每天都在期待下一期。」於此開始,謝銘祐慢慢把台灣的樣子一個一個拼回來,也成為了穩定他創作的核心。
在圖書館與葉石濤偶遇
大學讀圖書館學系,只因「看書不用錢」,謝銘祐下課後的時間也在唱片行、舞廳和酒店打工賺學費,書讀得多又廣,甚至曾經一個禮拜要訂七份雜誌,才能滿足圖書館藏書以外的求知慾望。某次借書時,謝銘祐在書架上偶遇葉石濤,憶起這位作家也來自台南,便將他的著作本本看過,「他影響我很大的,是某一些牽扯到族群和時代感的故事,我開始慢慢對這種跟歷史有關的台灣文學特別有興趣。比如《西拉雅末裔潘銀花》,她經歷清代末期、日本統治和國民政府來台三個不太一樣的階段,然後經過三五段感情。」葉石濤常借角色和細膩微小的事物書寫大時代,加上長期居住南部,經驗與謝銘祐疊合,兩人彷彿跨越時空走在相同的巷弄街區之中。
「族群這件事在我大學的時候還是很隱微,我們又經歷那時候的野百合,加起來就讓我更想要去知道一些什麼,也開始慢慢發現葉石濤的寫作的風格,好像是有一大塊鐵片壓在他的頭上。」謝銘祐描繪葉石濤筆下角色「簡阿淘」的壓抑,是連走在台南巷道裡都駝著背、緩慢而無精神,「我一直覺得他是隱身想告訴看書的人,其實我很沉重。因為每一篇作品交出去之前,都是要被檢查過的。」身作讀者,謝銘祐不只關注故事角色歷經什麼樣的時代背景,連同作者本身所處境遇,都需要被放入特定脈絡理解,「這樣的作者很努力想要讓你在字裡行間,嗅到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夠負責任的小說家,能帶你穿越時空
除了葉石濤,施叔青也是謝銘祐相當喜歡的作家之一,從《香港三部曲》到《台灣三部曲》,她的作品對故事背景的考據嚴謹而全面,在《行過津洛》這本書中更將泉州七子戲班的生活景況描繪得活靈活現。而擅長連結不同文本的謝銘祐,馬上聯想到了邱致清的《水神》,發現兩部作品對府城三郊商人建水仙宮以保佑貿易船隻的歷史描述一致,從而推斷兩者應是根據相同史料進行創作。謝銘祐之所以喜歡讀小說的原因便是:「如果這些小說家夠負責任,他真的可以帶著你穿越時空,在那個場景裡面跟著走一遍。」
在《行過津洛》故事中,令謝銘祐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段,「裡面提到以前要嘛新官上任,要嘛員外娶媳婦這種大事會開大戲,那時候台灣沒有戲班,他們會從泉州、漳州找戲班,然後會票戲。」接著,戲名、戲班名稱、開演日期⋯⋯這些資訊公告出來,從諸羅到恆春都會知道,人們就從各地沿途兜售家中農作物、慢慢走路聚集到府城看戲。「我很難想像那個情景。然後再去對照陳明章〈下午的一齣戲〉那一首歌。哇,這個地方好久沒有演戲了,今天要演呢!下午的時候大家都已經準備好,在等著傍晚的這齣戲,但你慢慢看到一片烏雲飄來⋯⋯」
接著大雨落下,眾人再無法看戲了。謝銘祐在文學裡讀見一齣戲在當年之所以重要的脈絡與情景,歌曲則透過旋律與簡單的詞句就表述出眾人失望的心情,兩者用不同的創作形式,立體化我們未曾經歷過的歷史。謝銘祐補充道:「當然絕對不是說,人不要往前走,而是我們連過去都不知道。」
宛如圖書館員的音樂創作者
喜歡同時看多本書且一邊記筆記,謝銘祐在文學作品中,只要看到厲害的形容或描述,就會停下來回頭琢磨自己的創作。他笑自己這樣的脾性也宛如圖書館員,能橫向、縱向地連結文本,將音符紡織為一座能哼能唱的時間圖書館。
透過音樂,謝銘祐將台南的街道寫成一幀時光定格的照片、一陣滷了一生的「肉臊香的風」,歌聲裡有過去的歷史,也有當下屬於這塊土地的人們的生活。
💬隻身前往孤島過一年會帶的那本書:
全套47期《人間》雜誌 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社
最想帶去的還是最愛的《人間》雜誌,整套帶去。這套雜誌影像多過文字,雖然也有很深度的報導文學,但那些影像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寫東西了。當年這些《人間》因為在同學間傳來傳去,後來一本也沒留在身邊,但我幾乎眼睛閉上,那些照片還是會跑進腦袋。
💬謝銘祐的台灣文學私書單:
1. 《人間雜誌》 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社
2. 《西拉雅末裔潘銀花》葉石濤,草根出版
3. 《台灣三部曲之一:行過洛津》施叔青,時報文化
4. 《安平兮烏龍船長》謝銘祐,三川娛樂
5. 《兒子的大玩偶》黃春明,聯合文學
6. 《水神》邱致清,麥田
About 謝銘祐
照片提供|謝銘祐
勘誤啟事:
誠品生活台南「寫予時間的記持|台灣文學慢板」展出中之「台南人的台文時間」展區,謝銘祐老師採訪專文中「謝銘祐下課後的時間也在圖書館打工賺學費」之段落有誤,正確內文為:「謝銘祐下課後的時間也在唱片行、舞廳和酒店打工賺學費」。特此更正,並向讀者及受訪者致歉。
回到_寫予時間的記持:台灣文學慢板
https://eslite.me/7k3j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