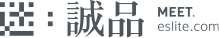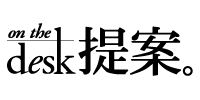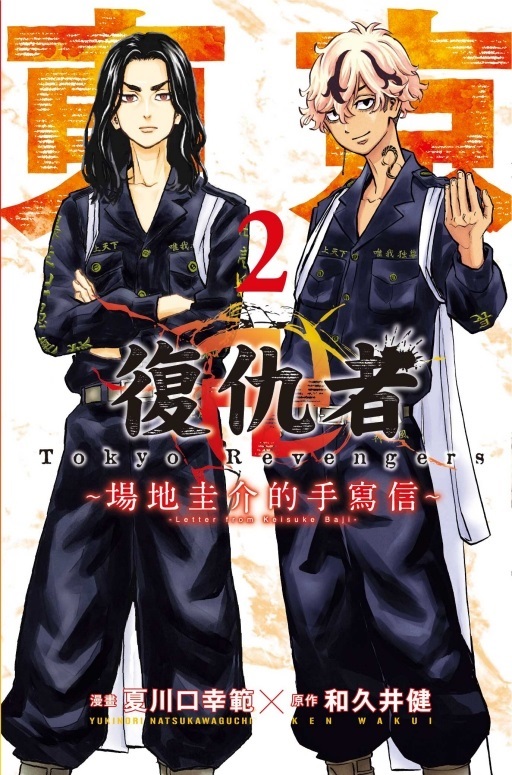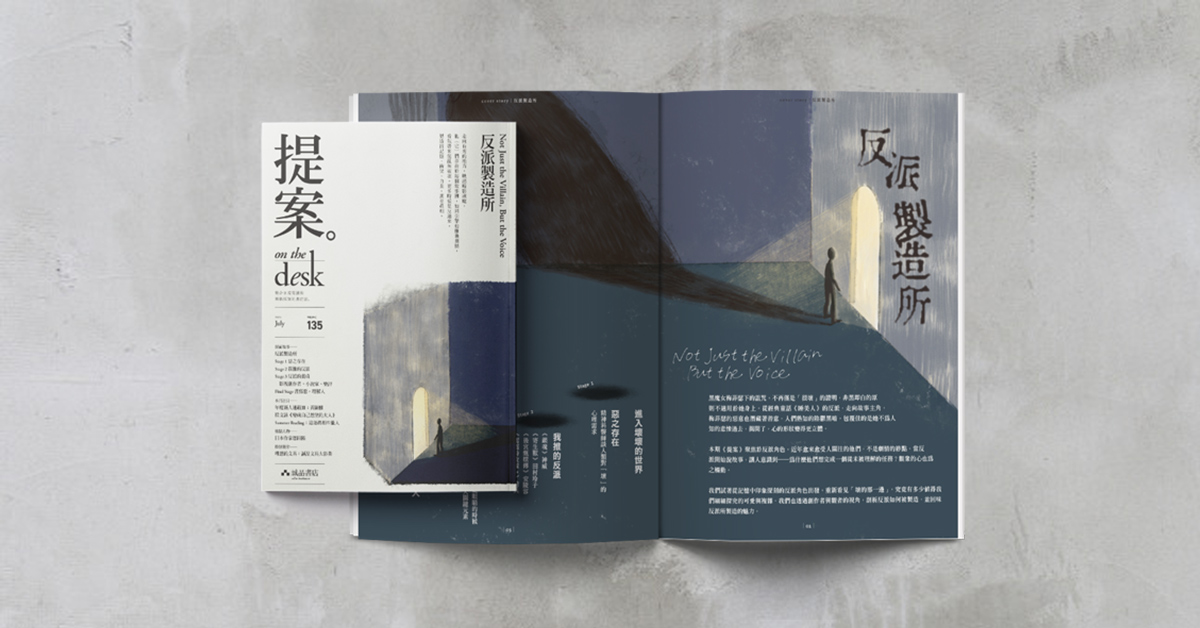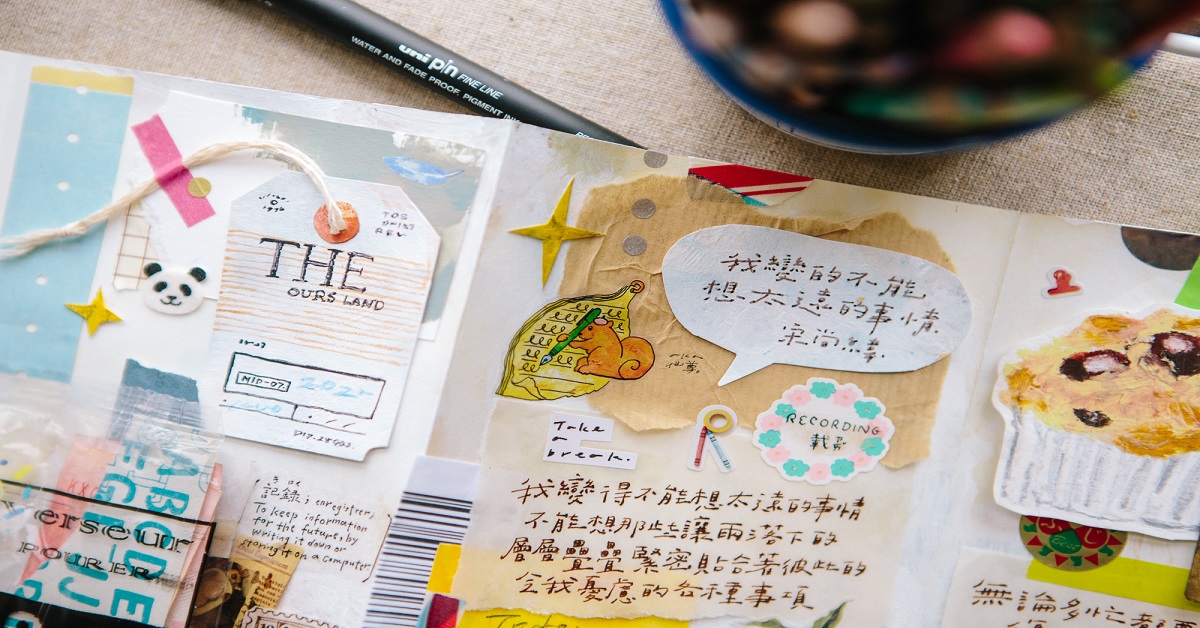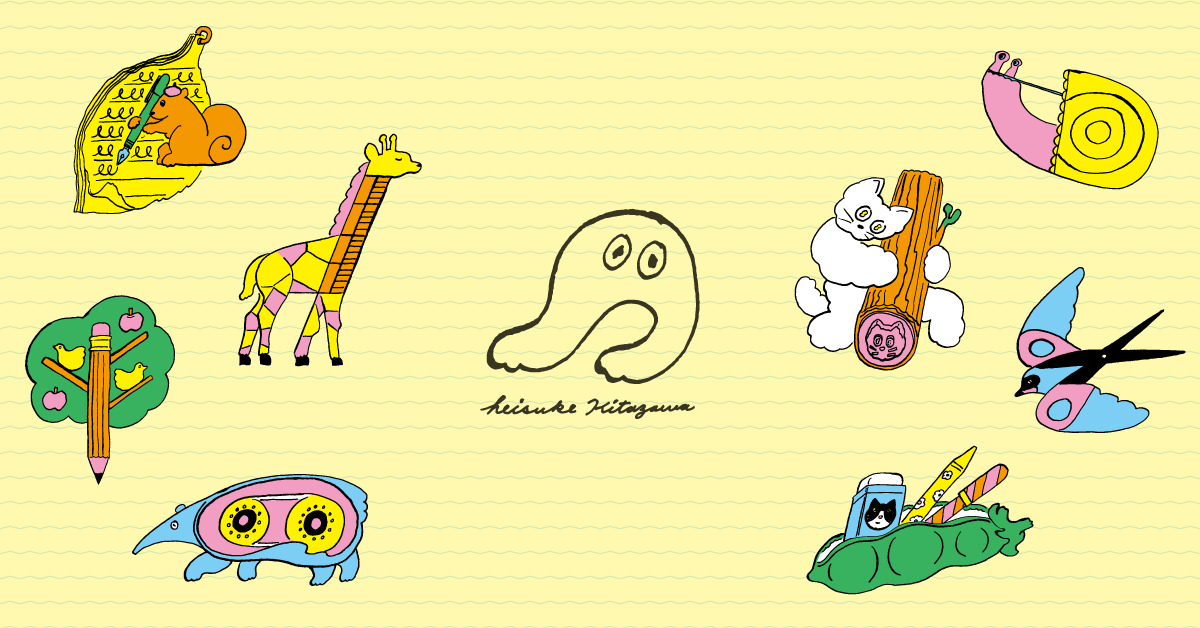當反派不眨眼睛的時候──專訪蔡家瑀導演
撰文 張嘉真.攝影|Ogawa Lyu.場地協力|二會咖啡此次專訪,導演蔡家瑀在訪談前做足了功課,帶來私心喜愛的眾多反派角色清單。對人性幽微始終感興趣的她,以創作者視角切入反派的塑造——資料蒐集、原型設定到角色定位,皆為使那個「壞」能產生情感連結而存在。那麼,一個會讓人念念不忘的壞角色,究竟要如何壞呢?

「他是對手,比你邪惡,還有可能是長久以來的敵人。」戲劇理論中「反派」的希臘文原文中有三種字根(註1),蔡家瑀將它們羅列出來,這樣的人,可以阻止主角行動,也可能創造主角的改變,它叫做反派。
作為一名編劇與導演,蔡家瑀對於人如何變壞、壞人如何使人著迷,如數家珍。蔡家瑀舉例《穿著Prada的惡魔》中梅莉史翠普飾演的魔鬼上司米蘭達,她處處刁難主角,嫌她土氣、嫌她的善良鄉愿,直到主角看破時尚產業決定離開,上司卻在主角唐突裸辭後,替她給出一個完美的reference check。米蘭達用她一貫霸道冷漠的本色說出:「她是我用過最讓人失望的助理,但是如果你不用她,你就是個白癡。」又或者是《色,戒》中梁朝偉飾演的易先生,他是女主角設局要暗殺的叛國特務頭目,易先生對他人冷酷、暴戾、充滿猜忌,最終卻動心買了一顆碩大的鑽戒送給女主角定情。刺殺行動敗露,易先生親筆批准處死所有同夥,包含女主角。她死後,易先生獨自坐在兩人曾經歡愛過的房間,茫然地看著空氣中的陰影。不同反派可能做了完全相反的選擇,卻都有那個共同的瞬間,踩中觀眾心中柔軟的一角。
「因為人隨時有機會變成壞人。」蔡家瑀形容反派的迷人之處在於,他們能夠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我們活在一個受到禮教壓抑的世界,反派卻能貫徹他的意志,他為了原欲、他為了貪婪、他為了他自己……」
蔡家瑀說,大家其實都很羨慕呀。
反派的執念,可能離自己不遠
然而有些主角的反派就是他自己。像是《黑天鵝》中的Nina與Lily、《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少年與老虎,「你不知道你其實是在照鏡子,一直到最後才發現,鏡中反射的那個陰影就是自己。」
蔡家瑀總是創造出這樣的主角。她喜歡人是有缺點的,從角色的瑕疵出發,她找到編導短片《箱子》莫子儀飾演的主角。獨自帶著女兒躲債的單親爸爸,誤傷害死女兒,他不知從何面對自己懦弱的惡,於是他把女兒的屍體裝在行李箱,日復一日對著箱子說話,與箱子過年,就像女兒還在自己身邊。直到有一天,箱子也不見了。「聽起來很荒謬,但是這個故事的原型其實是一則新聞報導的真實案件。」
蔡家瑀笑稱自己很喜歡瀏覽這些光怪陸離的新聞。社會新聞捕捉下來的報導,往往是十分特殊的情境,她因此能夠看見人會如何應對極端的狀況,「就像美只有一種標準,但是醜卻是千奇百怪的,人性有趣的地方也在於,善良是一種準則,作惡卻有好多好多形式。」有時候,變壞的過程是一種對於結構的回應。蔡家瑀舉例,如同《寄生上流》中的一家人,他們遇到最大的敵手並不是人,而是階級。當窮人越渴望翻身,就顯得富人的世界越可憎。在這個故事中,整個社會運作的形式才是難以撼動的反派。

細節養出不寒而慄的角色魅力
「人家都說魔鬼藏在細節裡,反派其實就是某一種鬼嘛,它也是透過細節建立出來的。」蔡家瑀熱愛觀賞犯罪驚悚的類型,從中取經如何打造一個壞的令觀眾信服的角色。
「我會要求我的反派不准眨眼睛。」蔡家瑀描述,這個細節是由《沉默的羔羊》中經典角色殺人魔漢尼拔身上觀察出來的細節。不協調的反應往往是反派角色與其他角色之間細微分歧的開端。這個人看起來與我們都一樣,但更用力、更仔細地看進他的深處,就會被他逮到。蔡家瑀信手捻來,接著分享影集《食人魔達默》,主角達默平常走路時,雙手不會自然而然地擺動,整個人看起來就像僵硬的機器人,但在達默把「獵物」帶回自己家中,準備殺人的那一瞬間會忽然動如脫兔。「那個反差,可能比他真的動手殺人,更讓觀眾害怕。」
從演員眨眼與否、笑起來時左右臉肌肉的對稱程度,到畫面上光學邏輯的調度——高對比、低曝光,將反派置放於構圖中的陰影處。問起蔡家瑀作為導演時,會如何對演員講解這個介在正常與異常邊緣的反派世界。她笑著說,演員只要搞清楚角色的目標與動機就能夠啟動表演,反派的執拗其實不過就是常人心中執念最大化的版本。我們每個人都能輕易成為反派。
*註1:從 Antagonist的希臘字意拆解出—對手opponent、邪派角色 villain、帶著仇恨與過節的對手rival,三種涵義可運用於戲劇創作。

一本聚合日常閱讀與風格採買的書店誌,紙本刊物每月1日準時於全台誠品書店免費發刊。每期封面故事討論一個讀者關心的生活與消費的議題,推薦給讀者從中外文書籍、雜誌、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
☞線上閱讀《提案on the desk》
☞雲端下載《提案on the desk》
☞《誠品書店eslite bookstore》粉絲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