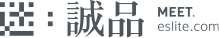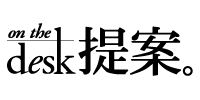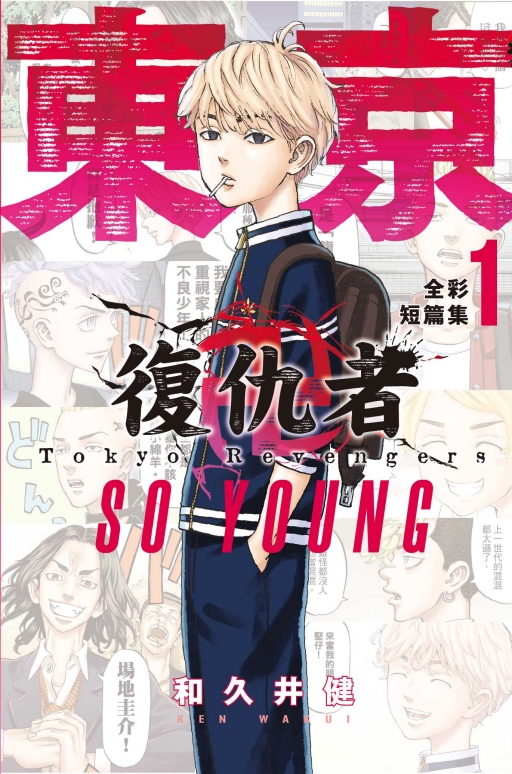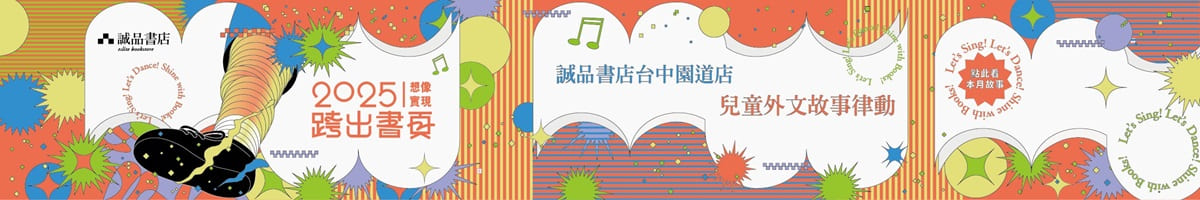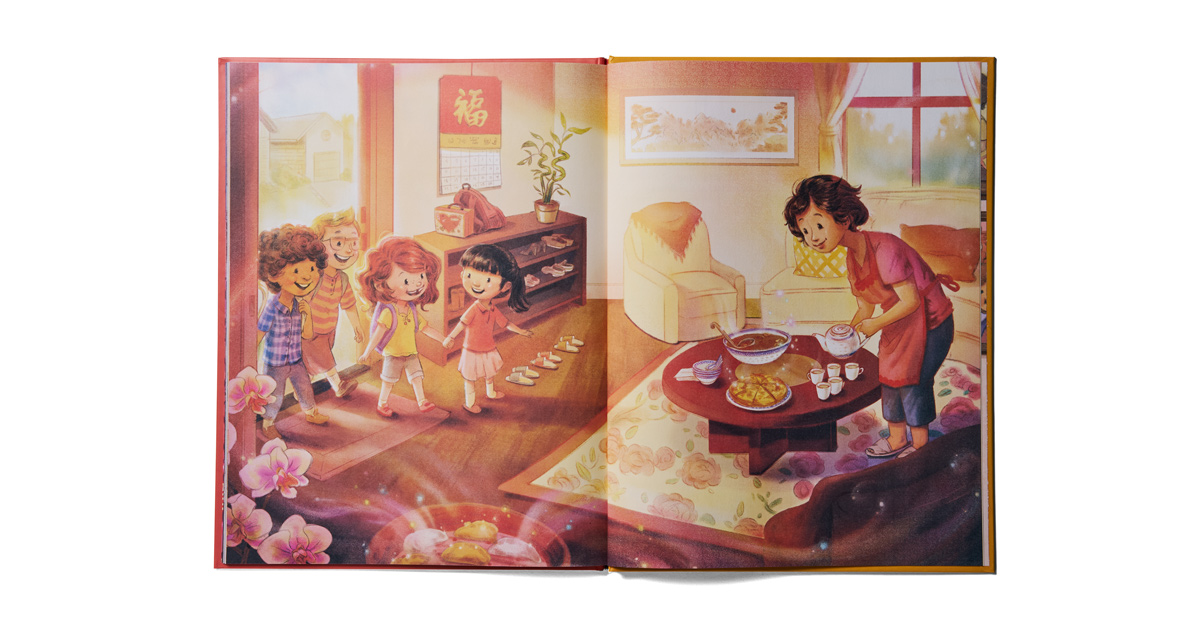恩田陆:即使感到痛苦,也要挑战过去从未写过的类型
撰文 盛浩偉.照片提供|筑摩書房
Q1. 您曾提过:「若不是写了《蜜蜂与远雷》,spring大概也不会诞生。」确实,这两部作品看得出一贯的精神,都以文字精准捕捉到其他艺术形式的核心,所以读起来栩栩如生,彷佛就正在享受着那些舞蹈、音乐一样。这次特别让人震撼的是,Spring当中钜细靡遗地描写了主角万春所编的舞蹈作品,但却全都是虚构的,就好像,是您透过文字在创作舞蹈一样。请问您这次的创作特地进行这种挑战,意图是什麽?过程中又是如何取得灵感的?
A. 这次的spring,我想描绘的不是主人公的成长,而是芭蕾舞本身。所以其中,也多少包含了我个人对「创作」这件事的看法,因此我将主角设定为编舞家,是想要透过他创作作品的过程,来讨论「创造事物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至於灵感,我自己是先接触到音乐剧和现代舞,最後才开始观赏古典芭蕾的,所以创作的过程,我脑海中是想着「好想观赏这样的表演」,然後就直接把脑海中浮现的东西写进小说里。
Q2. 在小说中,您也经常关注天才的存在。一方面,天才与旁人总是有一定程度的距离、多少带有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但是另一方面,您的小说中,总是能够找到彷佛伯乐一般的欣赏天才的视角。能否请您聊聊您自己对「天才」的看法?
A. 我对「天才」和「才能」这样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也会想要亲自体验看看有超群的才能是什麽感觉啦;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才能」的种类各式各样,而且不一定是肉眼可见的。一个天才的出现,需要有发现才能的才能、教导的才能、支持的才能、批评的才能等,是各种才能组合而成的复合结果。我对那种人与人之间、类似化学反应的关系很感兴趣,也深受吸引。
Q3. 在spring当中也描写到了天才的另一种面向:少数。被视为天才的主角万春自述他被学校这个系统视为少数异类、遭到排除,同时他的性向描写也带有同性恋的味道。您对「少数」是否特别关注?
A. 我从小就经常转学,总是担心在转学的新环境中是否能被接纳,实际上也经常被共同体排挤。我对那些规格外的、少数群体的一方抱有同感,我想这也投射在我的登场人物身上。
Q4. 在spring里,成为舞蹈作品素材的,除了音乐、文学作品之外,也提到了许多电影。您曾提过自己的阅读量大,要摄取许多养分才能有产出,想请问电影是否也是您平时汲取灵感的来源?能否谈谈几部您特别有印象的电影?
A. 我非常喜欢电影,从小就受到各种影响。有印象的实在太多了,无法选择,但学生时代观看後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去年在马伦巴》和《爵士春秋》吧。最近看的电影中喜欢的有《感应》、《璀璨女人梦》、《星期二》。动画《再见机器人》、Flow也很不错。
Q5. 请问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麽特别的习惯?写作这些需要大量从其他艺术领域取材的题材时,在田野的过程中有没有什麽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A. 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什麽特别的习惯。每次要开启一个新作品,都是既新鲜又可怕,之前的经验都派不上用场。而以「艺术」为主题时,我学到的是取材时观看大量作品固然重要,但放着酝酿的时间也很重要。即使看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产生不同的感想,把它化为语言的方法也会不同。另一方面,我也体会到「不要过度取材」很重要。如果满足於大量取材,那就没有想像的空间了。掌握这个分寸是最困难的。
Q6. 您出道成为小说家,迄今已经超过三十年。回顾过往到如今,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心境、关怀,有什麽变化?在完成了这些受到好评的大作之後,您还想要达成什麽目标?
A. 年轻时我拼命地写作,期待着如果累积大量作品、成为老手的话,就能够建立某种创作的理论,让写作变得轻松。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写作,我才明白这样的理论并不存在。我想,今後也只能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在每个时间点尽力而为,即使感到痛苦,也要挑战过去从未写过的类型。

spring
作者|恩田陆 出版|圆神
关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阅读与风格采买的书店志,纸本刊物每月1日准时於全台诚品书店免费发刊。每期封面故事讨论一个读者关心的生活与消费的议题,推荐给读者从中外文书籍、杂志、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
线上阅读《提案on the desk》
云端下载《提案on the desk》
《诚品书店eslite bookstore》粉丝专页
Current Issue_反派制造所
Not Just the Villain, But the Voice